我与殷墟
编者按语:
每周更新一次的“亲历殷墟,见证成长”感悟系列不觉间到了第十篇,也正是2022年新年第一篇。2022年第一篇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科技中心刘煜研究员,是考古所的才女,更是“半个安阳队的人”。我想她的妙笔生花,更代表了“殷墟考古人”的心声。
殷墟发掘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金石学的长期积累,古史辩派的批驳与反思,甲骨学的方兴未艾,新文化运动的引领,西方考古学的引进......诸多看似偶然的因素形成合力,使得殷墟成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第一代殷墟考古人是在田野中边干边学成长起来的,以“考古十兄弟”为代表的殷墟考古人更是那时中国考古学的真实写照,在殷墟这个即是摇篮,又是砺石上快速成长,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基石。新中国成立之后,殷墟考古发掘几乎未曾中断,殷墟同样承担着培养考古新生力量的重任。我们在见证三千多前年中华青铜文明鼎盛辉煌的同时,也要关注到“殷墟考古人”。考古十兄弟之一的石璋如先生就是典范,《殷墟发掘员工传》不仅详细介绍了当时史语所考古组的成员,更为参与殷墟发掘的临时聘用人员、当地村民立传,他们同样为殷墟考古发掘做出了程度不同的贡献,同样也是“殷墟考古人”。反思殷墟最近多年的工作,这方面的不足尤为突出!
万事开头难,本系列感悟目前更多聚焦在近些年在殷墟实习的学生,他们目前或在读、或工作,都对殷墟充满了感情,都认为殷墟是自己人生经历的重要一环,我想殷墟留给他们的,不仅仅是考古学知识,更有作为“殷墟考古人”的自豪感。希望以后我们能克服困难,把此系列感悟做的更广、更深、更持久。
我们这一生,会去很多地方,有些很美,有些很特别,有些很有趣。但是,总有些地方,因为承载着特殊的经历而成为心底永恒的记忆。
在我本人的时光地图里,安阳殷墟,无疑是其中最重要和特别的一个。它是我到考古所工作后接触到的第一个遗址,也是去的最多的遗址,安阳工作站的同事们戏称我是“半个安阳队的人”。每次走到工作站的大铁门前,看到那些巨大的箱子(整体提取的车马坑),听着门房熟悉的安阳话,“来啦”,一种踏实和幸福的轻松感就迅速笼罩了我,就跟回家一样。
安阳工作站有一个静谧的院子,我们住的楼前有几株粉色的樱花,一到春天就寂静而热烈地绽放。树下是一丛丛蓝紫色的鸢尾,舒婷写过的,“会唱歌的鸢尾花”,梵高画过的鸢尾,似乎没那么快乐,但是更加美。院子里还种了很多果树,有杏、梨、板栗、石榴,收获季节果实累累。牡丹开得最为娇艳,洁白、粉红、深紫,“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刘一曼老师很喜欢牡丹,曾经带着一个来实习的研究生和我一起走到殷墟博物苑去探访那里的牡丹,她记得每一株牡丹种在什么位置,开花的样子,是真正爱花的人。我们陪着刘老师在夏日傍晚的微风中慢慢地走着,听刘老师讲一些过去的故事,是特别惬意的时刻。

工作站的樱花和鸢尾

工作站的牡丹
曾经,在工作站的日子,是由杨锡璋先生的脚步声开启的。他总是第一个起床,插上电炉烧水,然后打好开水,站在院子大喊一声“水开了”。中午的时候,他会一路敲着饭盆,走到食堂,拉响吃饭的铃声。晚饭的时候同样的程序再来一遍。那种秩序感仿佛就是杨先生帮我们定下的,按时起床、努力工作、到点吃饭。吃饭的时候是最热闹的,有时加上实习的学生和访问的学者,两个桌子都坐不下。大家在一起谈天说地、讨论学术、聊聊闲话,一屋子欢声笑语。最美的时光仿佛就凝固在昨日,转眼间,说话“噼里啪啦”,脑子和嘴一样快的杨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九个月了。
岳占伟和付仲杨是和我同一年分到考古所的,因为是同龄人,我们很快就熟悉起来,小付后来去了沣镐队,最年轻的就只有小岳和我。刘忠伏老师爱开玩笑,说我是小岳的表姐,邺城队队长赵永红是表哥,总是笑呵呵的徐广德队长,是表二大爷。1998年夏天,我在安阳做殷墟青铜器保护的工作,正好赶上世界杯,大家看得如火如荼。英国和阿根廷的精彩对战,是我自己熬夜在会客室看的,看到了年轻的欧文横空出世。

跟李存信老师第一次到安阳工作

参与白陶的复原实验
工作站在暑期的时候最热闹,经常会有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学生来参观、考察、研究和实习。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的荆志淳教授和时任安阳工作站站长唐际根是二十多年的老友与合作者,至今还记得他们发现洹北商城的激动。老荆是一个非常热心、脑子特别聪明、精力也极其充沛的人,每次都会把自己新搜集的资料分享给大家,给他发邮件,无论有多晚都会收到他第一时间的回复。他和占伟一起合作制陶和铸铜的复原实验,到附近的太行山里找高岭土,收集牛粪,前者用来烧制白陶,后者则是猜想的殷墟陶范原料中可能的粘合剂。复原的陶窑不仅可以烧制陶器、烘烤陶范,在复原实验结束之后,还可以充当烤炉。这时候工作站里所有的学者、工人和学生,就会一起坐到月下的院子里,烤肉就啤酒,谈学术、聊人生,好不快活。

加拿大UBC的学生在制作用于青铜器铸造复原实验的陶范

荆志淳和岳占伟在开窑,取出复原的白陶器
荆志淳曾出现在何伟(Peter Hessler)名作《甲骨文》一书的开头,何伟说老荆的脸呈现简单的几何形状:“圆圆的脑袋,鼓鼓的双颊,圆圆的眼镜框。”何伟关于中国的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获得了很多人的喜爱和赞誉。当年他作为美国《国家地理》的撰稿人来安阳做采访的时候,我还跟他因为中国人到底如何看待电影《泰坦尼克》的问题争论了几句,因为英语不能完全表达出自己的意思而感到郁闷,早知道他的中文那么好,我就应该跟他用中文辩论了。
《国家地理》那一期用殷墟54号墓出出土的铜手做了封面,神秘、凌厉、震撼。这座殷墟二期的完整大墓,出土了很多高等级的青铜器,在研究过程中,我和北大的胡东波教授、杨宪伟老师一起用X射线探伤机拍到了青铜方尊铸造于外侧的铭文“亚长”,这是殷墟发现的第二件铭文铸造在器壁外侧的青铜器。此前,只有妇好墓出土的一件铜罐外壁铸有铭文“妇好”。柱帽具有特殊连接方式的方斝、热锻成形且表面錾刻八角星纹的圆盘形器、使用了焊接技术的铜盂,不断刷新着我们对安阳殷墟时期青铜制作技术的新认识。这前前后后的故事,都能在现任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的新书《亚长之谜:殷墟贵族人骨的秘密》里看到,我在为这本书所写的书评《走进牛尊背后的世界》里又补充了一些小花絮。
与安阳殷墟相遇的二十五年,是我自己寻找学术方向的一个发现之旅。我从最开始从事殷墟青铜器的保护工作,到使用多种理化手段对殷墟青铜器进行成分、金相等技术研究,后来的研究是将青铜器和铸铜遗物相结合,用多种方法探讨殷墟青铜器的制作和生产。在古文字学家严志斌和孙亚冰的帮助下,我还尝试将甲骨文、金文的记载与考古发现结合起来,探索关于工匠身份和生产组织管理的问题。
在安阳,我可以跟那么多人学习和讨论。至今仍记得杨锡璋先生给我画的夏商主要文化关系草图,也难以忘记陈志达先生介绍苗圃北地铸铜遗址的发掘情况。我向岳洪彬求教过殷墟青铜器的统计,也向牛世山了解过殷墟陶器的基本概况,老牛还给我找了特别多的参考资料。在学习阅读文献的过程中,我甚至会觉得跟那些大名鼎鼎的学者都成了老熟人,为石璋如、万家保、盖顿斯的研究而击节赞叹,或者,为李济、梁思永和夏鼐先生都是清华校友而有一丝隐秘的骄傲。安阳殷墟,就是那么一个能够任意连接历史和现实,无缝转换的地方。

带着学生去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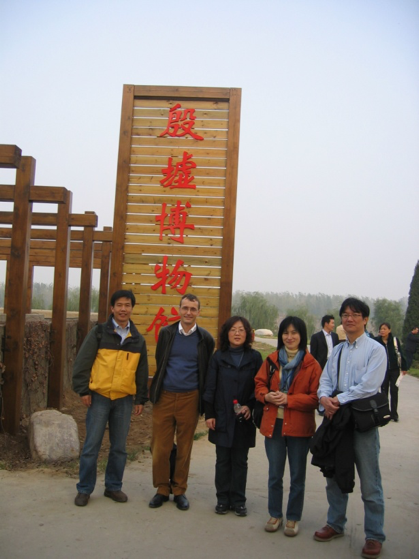
相会在殷墟
孝民屯铸铜遗址的发掘,无疑对我自己的学术工作有重要影响,我和岳占伟、岳洪彬、李永迪、内田纯子等人的合作,始于此,我的博士论文的写作,亦始于此。常怀颖还开玩笑说,他认识我,并不是我被北大陈建立教授请去上课的时候,而是我跟苏荣誉教授一起被领队王学荣请去考察孝民屯铸铜遗址的时候,那时候他是学生,在探方里发掘,看着我们在地面上走来走去。
科技中心的同仁几乎都跟安阳队有深度的合作,我其实特别期待看到其他人对安阳的回忆。于我,这里是学术的宝库,也是温暖的家园。我有很多次的生日都是在安阳过的,他们帮我买过蛋糕,也办过烤肉party。办公室主任崔良生是安阳队的大管家,帮我们解决各种工作和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有一个加拿大的女学者很喜欢出去喝点啤酒,我就充当他们两人的翻译,她一口一杯,把整个酒馆都震了。我喜欢吃苗娜做的包子、炒饼和面条,面条一般有两种卤,西红柿鸡蛋和蒜台炒肉,都特别好吃。三妞、艳丽、慧君、刘小贞、尾(读以)巴、毛玉和他的儿子卫国、合子、李玲、老建、国子、老梁,还有很多人,有些我也叫不上名字,他们的笑容此刻在我面前次第展开,温暖而明亮。
安阳是一座有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城市,我喜欢以安阳为背景的电影《孔雀》,也喜欢痛仰乐队的歌曲《安阳》。“所有的人都醉了,请为我点盏灯火。在夜里轻轻歌唱,回忆是淡淡忧伤。安阳安阳,别离的话不要多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