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从历史长河中的鸟瞰位置远眺——读《第五次开始:600万年的人类历史如何预示我们的未来》
在怀大联培的一年间,笔者曾经不止一次地向罗伯特·凯利教授讨教,究竟是怎样的力量驱使人类建构起名为“国家”的社会组织形态。而他的回答至今依然发人深省——“我们通常不会纠结于某一史前聚落的社会组织形态究竟是仍然属于复杂酋邦抑或已经步入早期国家的行列,而将更多的注意力投注于组织变迁本身以及这种变迁所处的人类历史潮流。”前者要求研究者具备“通过整理细节,尝试发现浩瀚森林的模式”(38页)的细腻心思,后者需要研究者拥有“从历史长河的鸟瞰位置远眺”(158页)的广阔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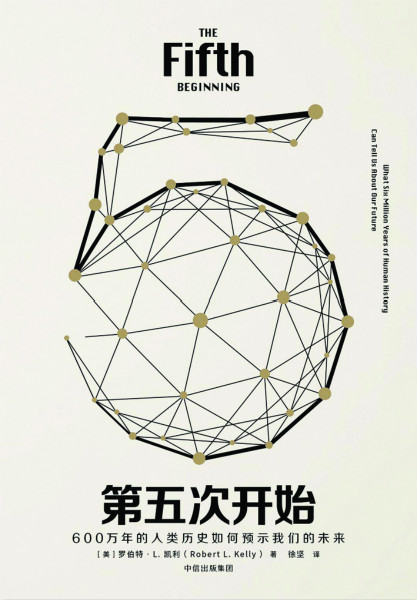
而“当你从历史长河中的鸟瞰位置远眺”——这句话也一遍遍地出现在了这本《第五次开始——600万年的人类历史如何预示我们的未来》之中。作为考古学家,可能这也正是该书最想传达给大众读者的的独特视角:“考古学提供了人类历史的关键记录。对于我们的历史的绝大部分而言,它是我们拥有的唯一记录。然而,如果你阅读世界历史书籍,你可能发现史前史只出现在第一章,甚至可能是第一章的第一段。教科书里,历史常常从埃及、希腊、罗马和中国‘文明’开始。史前史不过是舞台布景:‘现在你看到猿猴,有的离开树枝,降落地面,直立行走,我们的大脑逐步增大,我们制造石器,绘制洞穴艺术,栽培小麦’——接下来进入真正的历史,重要的东西。但是,将史前史贬低为背景,历史学家就错过了历史全景”(12页)。
那么,以历史全景为舞台,在《第五次开始》中又为我们带来了怎样的人类学思考呢?笔者以为,从生物进化论到文化进化论,进化论的思想贯穿了全书始终。书中“将进化理解成为不同的生物结构或行为之间的成本和收益的权衡”(58页)。这里的“进化”所指显然是生物学范畴内的优胜劣汰,但是权衡成本与收益的内涵却道出了更为广泛的进化内涵。不论是物种抑或是文化,“人口增殖带来的竞争加剧是最主要的驱动力”(7页),面对竞争、优化选择,则是进化“主体”于客观上长期存续的基本方针,人类史乃至人类社会史正是一场“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之下的生物—文化进化史。
在过去的600万年中,这样的进化人类经历了四次,书中称之为“开始”。按照时间顺序,它们分别对应于技术、文化、农业和被称为“国家”的社会组织形态——“使用石器的更新世祖先战胜了不用者;拥有文化能力的战胜了缺失者;农夫最终超过了狩猎—采集者;酋邦和部落臣服于国家社会,后者迄今仍然统治世界”(6-7页)。然而,“栖居在树端的灵长类动物并无意于成为直立行走、使用工具、狩猎的古人类。这些古人类也没有想过成为使用符号、讲述故事、呼唤灵魂的人类。狩猎—采集者没有立意成为农民,农民也没有打算成为帝国一员。通过历史,我们只是竭尽全力,做最好的自己:最佳树居灵长类动物、最好的使用工具的古人类、最好的狩猎—采集者、最好的农业村落首领”(215页)。而意欲成为“最好的自己”即须完善“成本与收益的权衡”。
回到技术的“开始”之前,“自然选择有可能最终导致灵长类拥有咬合力强大的下颌,可以咬断大型动物骨骼,吸取骨髓,或者长出可以舔刮动物尸体上残肉的牙口……但是,如果考虑到灵长类头骨形态、肌肉和牙齿形态需要做出多大的变化时,就知道几无可能”(59页)。换言之,在这样的进化选择中成本要高于收益。“另一方面,发展出技术的生物可以跃过生物选择的漫长过程,跻身进化序列的前排。石器的成本和收益告诉我们,在中新世晚期的竞争环境之中,人类就这样增加了猎物,从几乎是进化链最底层的混乱之中脱颖而出”(59页)。
在关于文化的“开始”的思考中,该书将其理解为“由一群人共享的一系列观念和信仰”(101页),这与尤瓦尔·赫拉利先生在《人类简史》中对于“认知革命”的解读基本一致,即可以“一起想象”的“虚构的现实”。精彩的是,《第五次开始》更为细致地观察了“讲故事”的能力的形成条件与机制,即“前瞻性思维,以及在智力意义上,将不同部件拼缀成为统一、有序的整体的能力”(87页),并以多层意图的架构形式展现出来。具体而言,语言沟通与工具生产(阿舍利技术、细石器技术)为文化的“开始”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训练,而艺术(三个层级的意向性:“有的人希望其他人知道他们知道生活并不如他们所期待”(95页))与宗教(四个层次的意向性:“我知道你知道我们共同理解神祗认为我们应该按照特定方式行动”(102页))则直接标志了文化的“开始”。反映至“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层面,多层意图的架构产生的“认知能力之一是‘施动者侦测策略’,即允许我们领会其他行为者的意图的能力。作为社会性动物……这是群居生活的关键能力”(103页)。“因此,我们相信,对世界的‘意义’的共识必将使具有文化能力的古人类比缺乏文化能力的古人类获得更高的繁衍适应性”(108页)。而当前者面对初建共识的内容选择时,“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促使以“合作”为主旨的共享理念成为了人类社会最早的核心价值观——“我们曾经经历的自私和无私之间的拔河比赛表明,我们可以计算两者的得失。自私行径自有好处,但是在文化环境中,无私行为也是如此。如果文化的力量允许创造象征性建构的宇宙,如果人类能够看到慷慨有利,慷慨就会得到文化强化,而更为常见”(110页)。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拥有文化的群体成员可以创造合作联盟,帮助他们度过干旱和其他时艰,因此人口继续增长。有的离开非洲,战胜了诸如尼安德特人等其他早期人类。成功的代价是生存空间的竞争”(223页)。具体而言,“狩猎—采集者维持着不断降低的回报和迁往新营地的成本之间的平衡”(132页)——“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有人捷足先登,占领了下一处营地的可能性也在攀升。在这种情况下,狩猎—采集者有两种选择:将其他人从心仪的土地上驱赶出去,或者留在当前的营地,丰富扩充你的食谱。前一种选择很冒险,因为你可能战败。后一种选择来自饮食幅度模式。如果你已经耗尽了排名靠前的资源,就必须将低回报资源纳入饮食之中”(133页)。再次面临“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农业的“开始”适时启动——“气候变迁和偶然的植物基因变异导致农业成为可能的选项,而狩猎—采集者把握住了时代契机。在地质时间上不过是短短一瞬,狩猎—采集者就成为农民,创建出定居村落”(152页)。
随后,“垦殖将人口绑缚在土地上,有的人发现为了生存,他们需要控制其他人的资源和劳力”(223页),同时也就“需要向自我和别人‘解释’为何他们应该占有更多。这就是人类学家所称的‘意识形态’,解释不平等的信仰系统”(208页)。正是在这样的信仰系统的支配下,国家的“开始”得以发生。问题是,面对“资源和劳力”的让渡,所谓的“其他人”又因何接受并甘之至今呢?无外乎于“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当“意识形态”成为文化的边界,便似“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昼日之颜哪怕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也都只是官方准许的色彩;然而,拒绝“意识形态”,精神的世界却也未必就能焕发出更多的光彩,失去了曜日之辉,我们所能收获的恐怕将是无穷无尽的黑暗——意识形态与文化能力的捆绑关系最终促成了“政治臣服者”与“文化流浪者”之间的尖刻选择(事实上,这几乎无需取舍,自我们的先祖获得文化能力之刻起,后来者便已失去了自主放弃这项能力的机会——我们可以选择看待世界的立场,却无法放弃“拥有立场”),前者则在“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之下屡屡胜出。
第五次“开始”,该书认为,正值当下:“一个剧变的时代,是继技术、文化、农业和国家开始之后的另一个伟大转型的时代,一个全新的开始”(222页)。而进化则似命运的齿轮,依然维持着它既有的步调稳步向前——全新的时代赋予了人类文化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同时也打破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地理分界,伴随防御纵深的日益缩减,文化冲突必然不断升级、范围亦将逐渐扩大,不论积极或被动、觉悟或蒙昧,文化生态圈的战国时代已然来临。那么,再次面对“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我们又该如何抉择呢?依然是“竭尽全力,做最好的自己”,书中称之为“简易模式”——“意识到世界发展的方向并且完成这个发展。”首先,不同于生物进化依靠自然淘汰完成选择,在文化的“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中,受众虽然同样无法脱离现世的因果,却已由被动的接受转变成为自主的选择;其次,“我们有自我教育的历史”(254页),政治文明有能力通过“自查”“自省”及时调整对于组织结构的认知、未来蓝图的规划,“意识到世界发展的方向”;最后,“人类现在已经拥有改造世界的能力”(253页),“如果我们拥有摧毁世界的能力,那么我们也可能拥有创造世界的能力。这意味着制造、存储、转换和使用能源的地质工程与新方法。但是,这也意味着组织我们自身的方法,扬善惩恶的方法”(254页)。而这正是“完成这个发展”的方法。
《第五次开始》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历史全景的绚丽长卷,而贯穿其中的则是进化理论的质朴气韵。诚如作者所言,“人类进化一直是,而且应该是,甚至必须是由我们自己掌控的”(254页)。吾辈作为第五次“开始”的见证者与亲历者,自当知往鉴今,以启未来。
(图文转自:中国文物信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