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际根:关于殷墟人骨DNA和殷墟人种问题我想说几句
3000年前的商王朝像一个谜。我们都很想知道那些使用甲骨文的人是何方神圣,当然也想知道妇好是什么模样。长期从事殷墟发掘的我自然不例外。
当年撰写《中国考古学·夏商卷》时,商族人种的部分是我执笔总结撰写的。199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于商族的的人种,是通过“体质人类学”的手段定位在“蒙古人种东亚类型”这样一个论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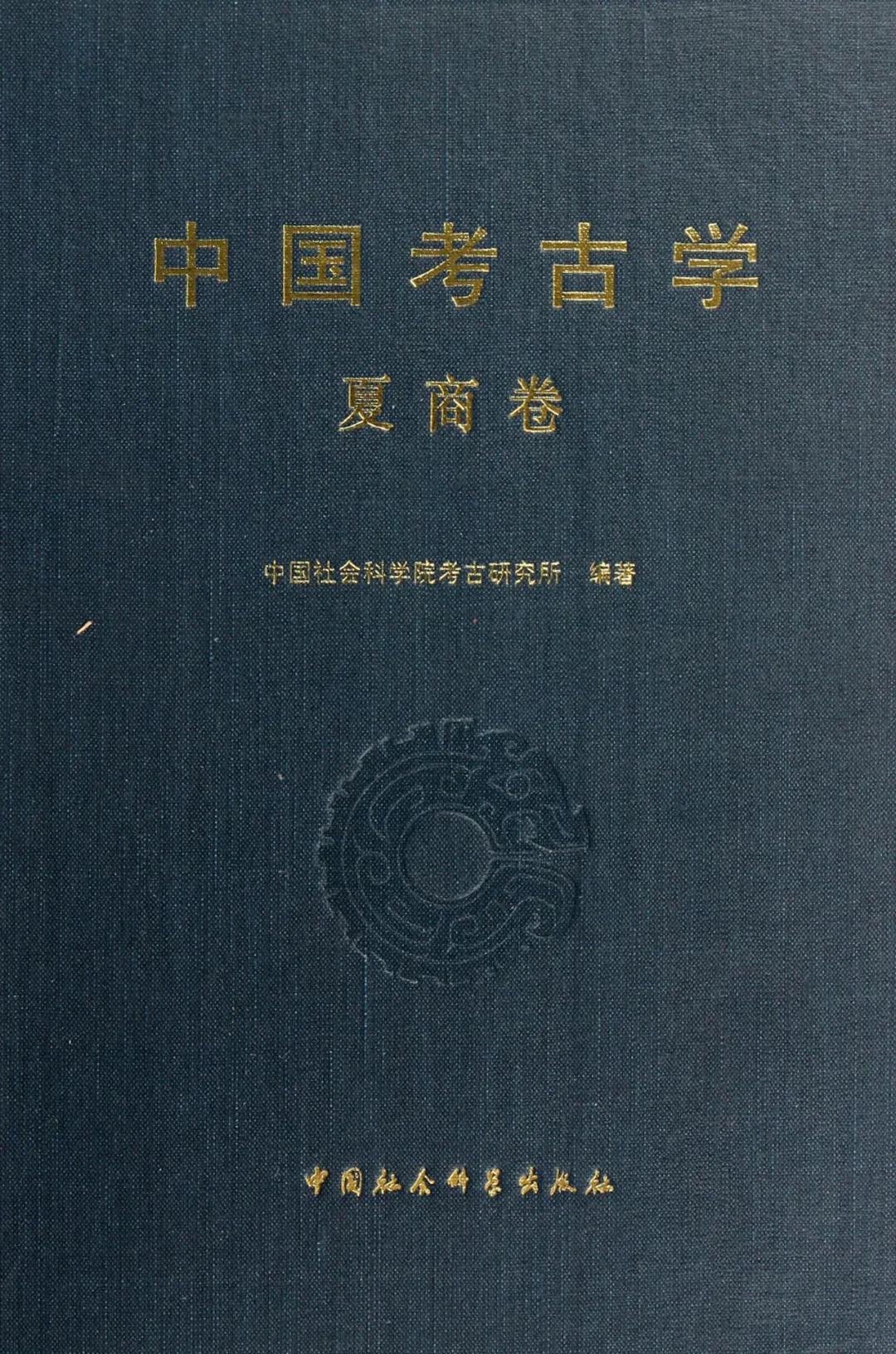
1992年,我在殷墟“新安庄墓地”发掘,清理了100余座商墓,其中约半数保存有人骨。当时便想通过这批材料做点新研究。那时我没有按前人习惯将人骨取回室内后再研究,而是请体质人类学家韩康信先生直接到现场,挨个鉴定墓坑中的人骨,包括年龄与性别。
当时的通行做法是以长骨指数法推算死者身高,我觉得指数法不如直接测量人骨架准确,于是逐个人架测量。后来我常说,商代男子身高的中位数只有1.62米左右。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便是对新安庄墓地商人骨架的测量结果。然而新安庄人骨的研究,并不包括基因测试。后来我有机会获得另外一批新材料,才开始的殷墟人骨的DNA研究。
1997年,根据国家文物局批示,安阳队在殷墟西部“黑河路”实施发掘。这次发掘清理了约100多具商代人骨架。1997年与1992年虽然仅隔5年,但学术界的科研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数年之中,德国、日本等国以基因技术研究古代人骨标本并取得显著成果,燃起了我想以DNA技术揭示商族人种的希望。
当时吉林大学基因实验室尚未建立,国内能看到的古DNA研究成果,只有古脊椎所刘武先生与公安部的合作。然而此前一年(1996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了殷墟研究的一项国际合作,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合作。合作项目的主要实施者有我本人,还有荆志淳教授和志淳的老师Rip Rapp教授。
某日,Rip转给我两篇发表在Science的论文,是西方学者通过基因技术研究古人骨骼的案例。我读后感触更深。1997年,Rip推荐当时在加拿大Lakehead University基因实验室从事分子生物学和古人类研究的学者El Moto到中国。在我的安排下,El Moto在安阳工作站花了约一周时间观察殷墟“黑河路”的商代人骨。我们当时计划双方对“黑河路”人骨开展一项专门的DNA研究。但研究之前需要另签协议。
凑巧的是,在我们与美加学者签协议前,中国科学院基因研究所的基因学家W和J(因未征得他们本人同意,我暂以字母代替其名)主动找到我,希望合作开展殷墟人骨的基因测试。我们讨论后,决定选取少量商代人骨标本,先将实验做起来。必须说明的是,当时我选送的标本正是El Moto帮助整理过的标本的一部分。
不久实验完成。W和J专程赶到安阳展示实验结果。令我震惊的是:我选送的黑河路商墓人骨,其基因检测结果接近此前日本学者所做的西亚人骨。W和J由此推测殷墟商人可能与西亚人相关。
2000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金台饭店召开学术会议,W曾简短说明其基因测试结果,但由于作为合作者的我态度谨慎,W当时在会议上也采取了保留态度。具体的实验数据,我想应该由W和J亲自公布。他们是实验完成者,是真正的基因专家,而我不是。
这就是所谓“殷墟人骨是西亚人种”的大致过程。
W和J的测试结果,直接与此前体质人类学测量所得出的“蒙古人种东亚类型”结论相悖。通常情况下,我应该继续与W和J共同研究,或者尽快启动与El Moto的合作,但接下来两项工作都未延续。这可能是导致今天有朋友向我发问的原因。为此我说明如下:
1我为什么对“商族人可能是西亚人或高加索人”的推论充满疑虑
我确实在一些小型演讲或者研讨会上说过,我本人不大相信“商族人可能是西亚人或高加索人”的推论。
我之所以对当时的研究结果有所保留,主要因为当时纳入研究的标本数量少、质量也存在一定问题。
标本数量少,一方面是选送的殷墟标本数量本身就少,但另一方面,甚至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当时可供比较的reference少。在当时全国夏商遗址人骨DNA数据大面积空白的情况下,“西亚”人骨数据作为几乎仅有的对比数据,显得比欧美数据更接近殷墟毫不奇怪。这种情况下“对比”出来的结果,我们必须慎重。如果当年的中科院遗传所积累了今天吉林大学古DNA实验室这样的数据量,我想我应该不会担心吧。
如上所述,我选送的标本,曾经是加拿大学者El Moto接触过,El Moto作为白人的基因是否会通过接触残留在标本中?如有残留,这些残留是否会影响的测试结果?这些我都无法作出判断。因此我不能轻易表态。
当然,已有的考古知识也无法让我相信“商族人可能是西亚人或高加索人”。且不说文化传统、文字使用,只说发掘出来的一些真正的“商朝人形象”。
我曾有意识地收集殷墟出土的各种“商代人像”,包括人体圆雕、浮雕、半浮雕、平面图像。我收集到的以图像形式表现“商人形象”的作品近30件,没有一例是“西亚人相貌”或者“高加索人相貌”(下图)。

我认为,这些作品是商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自我形象的表达,应该真实记录着商族人的种族特征。它们完全不支持“商族人可能是西亚人或高加索人”的结论。

2 为什么我没有继续坚持殷墟人骨的DNA研究
有朋友认为,我“发现(商王朝)王族可能是白人”,于是“就不让做DNA”。
这是误解。我的确不大相信“商族人可能是西亚人或高加索人”的推论,但这不是我中止殷墟人骨基因研究的原因。
有朋友说我“一辈子努力都是给我们中国人找个优秀祖宗”,“自己心里接受不了这个结果”,这实际是“抬举”我。实际上,我只在乎研究结果是否实事求是。
殷墟人骨的DNA研究后来之所以未能继续,是多重原因导致的。
“西亚人”的推论使我意识到基因测试的重要性、复杂性和敏感性。我当时的心情是,项目一定要继续做下去,但要设计好、准备好。新的基因测试要慎之又慎、认真准备。准备不足就不重启。
在我看来,人骨DNA研究的准备工作要从发掘开始而不是从采集标本开始。我们要选对标本的考古背景(例如并非所有出自殷墟的人骨都是商族的);我们要认真处理样本的污染问题(既有可能发生在发掘过程中,也可能发生在采样过程中);我们还要充分考虑到人骨的保存状况。
出于对困难的顾虑,我几次“重启”基因研究的想法最终都中途放弃了。
田野工作重心的转移,是影响“重启”的另外原因。1999年我和安阳队的同事们发现了洹北商城,工作重心转移到洹北商城的结构、年代和布局等工作上。洹北商城的工作告一段落后,又赶上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我精力有限,只好将殷墟人骨的基因研究放下来。2009年,我曾想过重启基因研究,然而那时我又承担了中国社科院重大科研项目“殷墟布局的探索与研究”,基因研究再次被搁置。
还有一些客观原因也影响了重启殷墟人骨基因研究,例如后来我国有了DNA样本出境的禁令,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开始筹建自己的DNA实验室等等。
3 顺便说一下殷墟人骨基因研究的复杂性
考古学发展到今天,通过基因测试研究古代人骨标本逐渐成为常规手段。殷墟人骨确实需要基因测试,但殷墟人骨的基因研究并非只是“提取基因(片段)”这么简单。如何“提取商族基因(片段)”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作:如前所说,并非所有发现于殷墟的商代人骨都是商族的;“商族”是否等同于“王族”也需要讨论。有句话说出来可能令大家沮丧:殷墟的王陵大墓早年都被盗掘,1930年代又被挖了一次。或许我们早就失去了找到“商王”基因的机会。
基因研究要从发掘开始。如果妇好墓的发掘不是发生在1976年而是今天,或许我们还真能找到妇好的基因。从而认识“生物学上的妇好”。
商族基因的研究必须系统规划。殷墟的人骨标本非常重要,但仅仅盯着殷墟远远不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跟随张光直、张长寿等先生参加商丘田野考古,去豫东寻找“先商文化”。今天看,当年寻找“先商文化”的工作也应该与殷墟人骨的研究联系起来。
我们应该严肃认真地考虑组织新一轮的“商代人骨基因工程”。这一工程的工作对象,应该包括殷墟、洹北商城、郑州商城、二里头,甚至应该包括三星堆等同时期其它遗址。
感谢各方人士关注殷墟、关注商王朝。
责编:韩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