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武扬威:权杖源流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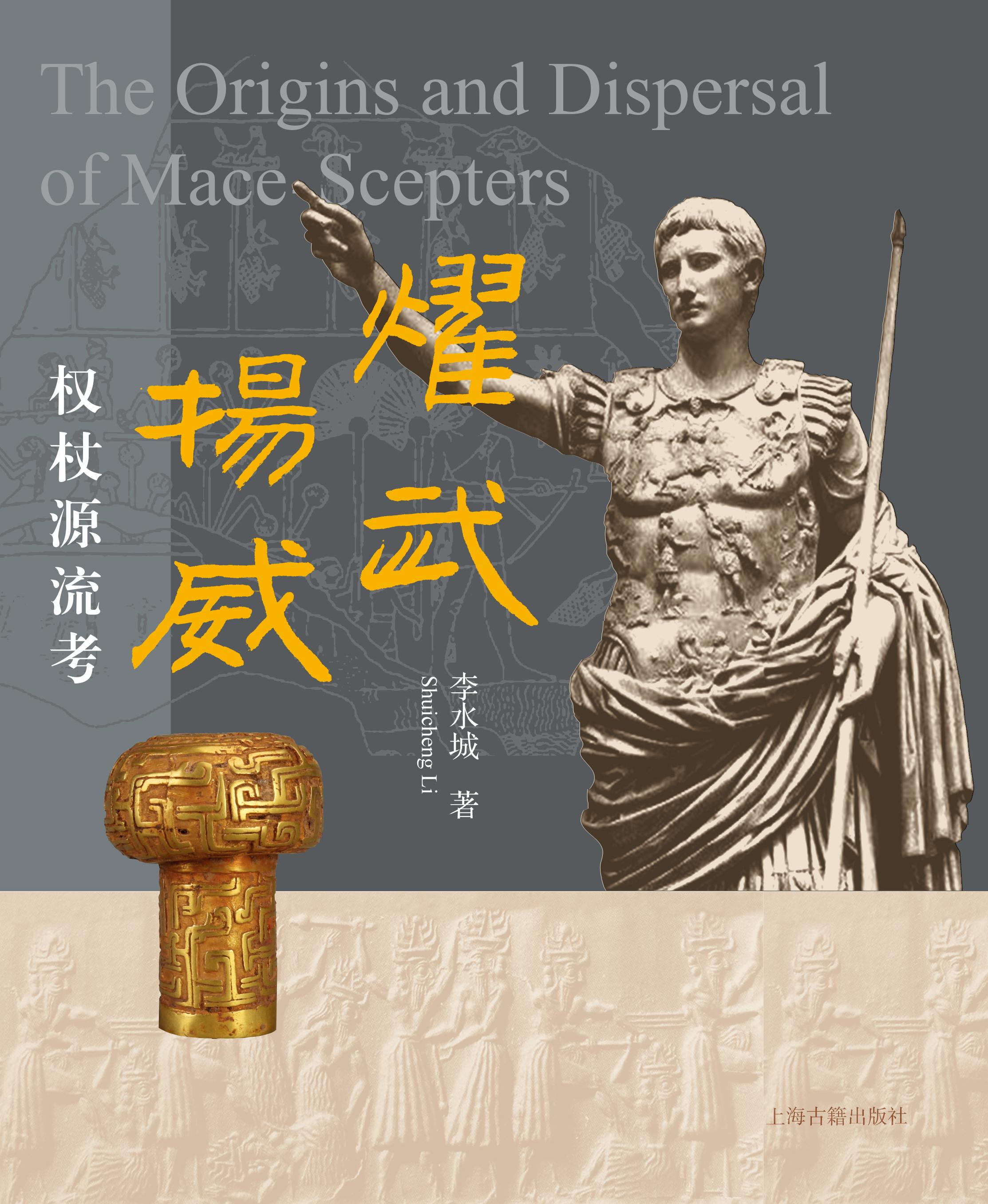
基本信息:
作者:李水城 著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4月
版次:1
印刷时间:2021年4月
印次:1
ISBN:9787532598571
作者简介:
李水城。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学士(1982)、硕士(1988)和博士(1996)学位。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1999)、哈佛大学(2000、2015)、剑桥大学(2006)、牛津大学(2016)做访问学者。现任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已出版专著有《半山与马厂彩陶研究》(1998)、《中国古代陶器》(2001)、《东风西渐:中国西北史前文化之进程》(2009)、《正业居学:李水城考古文化论集》(2017)、《中国盐业考古》(2019)等。
内容简介:
权杖产生在距今1万年前,是一种具有双重功能的文化特质。最初权杖作为工具或兵器出现,后来随着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加快衍化出新的功能,即作为社会上层人物秉持的礼仪用具和具有“魔力与威能”的王权象征。权杖之发展,犹如历史的一面镜子,折射出人类社会自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以来,各大陆之间的族群迁徙、文化交融与互动,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革及观念意识的传播与扩散。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考古发现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中国,西亚、中亚、南亚、北亚,北非,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出土的权杖(头)做了全面介绍。下编为比较研究篇,内容涉及权杖的起源、制作工艺、功能、传播以及权杖传入中国后的命运等话题,并对一些与权杖类似或功能接近的器物作了相关的介绍和分析。
推荐语:
严文明 李零 杨泓 冯时 联袂推荐
2000件神秘权杖,横跨五大洲,一部王权与神权视野下的东西文化交流史
以往在中国,一些遗址出土的权杖(头)因不明用途而不被重视。李水城将此类遗存搜集整理出来,并与国外所出权杖(头)作了深入比较,不但将其功能讲述得清清楚楚,而且见微知著,论述了此物的起源、传播以及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难得。这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力作,特此推荐。
——严文明(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西来的“权杖”后来未能在中国流行,其原因恐怕在于古代中国有完整的“礼制”,帝王行为器用均要遵从“礼制”,这一点与以环地中海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完全不同。水城通过权杖的研究,总结出华夏文明对外来文化取舍有度、伸缩自如的认识,是很有见地的。
——杨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权力的象征物有两样最典型,一曰权杖,二曰斧钺。这两样都是从最原始的武器(最初也是工具)发展而来,全世界都用它们象征权力,用于征伐或惩罚。水城用“耀武扬威”四字概括之,透物见人,遗形取神,即小见大。传统兵器研究,似乎还很少从礼仪的角度作深入探讨。其实,除了权杖,还有很多兵器也用于礼仪(如卤簿仪仗),象征性大于实用性,今后值得拓展研究。水城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
——李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考古学研究的世界视野,使我们有机会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认识己身文明,西学东渐的观察视角早已为人们所熟悉,其实中学西渐提供的思考同样不可或缺。李水城教授的这部著作充分展现了作者在这两方面的用心与作为,卓尔不群。
——冯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目录
自序
楔子
上编 权倾依杖:中外考古发现
壹/东亚的中国
西北地区•甘肃
西北地区•青藏
西北地区•新疆
中原地区
北方长城地带•西部
北方长城地带•东部
东北地区
淮河以南
小结
贰/西亚
安纳托利亚
黎凡特
美索不达米亚
伊朗
叁/中亚、南亚与北亚
中亚
南亚
北亚•西伯利亚与蒙古
肆/北非尼罗河流域
尼罗河下游之古埃及
尼罗河上游之努比亚
伍/欧洲
西部欧洲•东南欧
西部欧洲•中欧和西欧
西部欧洲•北欧
东部欧洲•高加索地区
东部欧洲•东欧草原
陆/美洲和大洋洲
美洲
大洋洲
下编 权重执杖:比较研究
柒/权杖的起源和制作工艺
起源
制作工艺
捌/权杖的功能
工具•兵器
权力象征
神圣祭品
随葬品
玖/权杖的传播
西亚
欧洲
北非之埃及
中亚
北亚之西伯利亚
小结
拾/权杖在中国的命运
来源
形态、功能比较
权杖对中原王朝的影响
斧钺传统与帝国政治
商周时期的“殳”
汉代以后的孑遗
拾壹/类似权杖之物
短柄石棒
杆头饰
其他相关遗物
结语
参考文献
主题索引
插图索引
附记
楔 子
权杖,英文称MACE或SCEPTER,俄文称БУЛАВА或ЖEЗЛ。此器由器柄和权杖头两部分组成,器柄多为木质,少数为石质,或用金属铸造。权杖头安置在器柄顶部,以石质为主,或为金属质地,也有少量用其他特殊材质制作。根据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和民族志资料,权杖的造型多种多样,差异较大,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民族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共同特征是在杖柄顶端都安装有形态各异的权杖头(mace-head)。
Mace,这个英文单词的本意是指生长在热带的一种常绿乔木植物果实,即肉豆蔻,又名肉蔻、肉果、玉果或麻醉果等。肉豆蔻树原产于东南亚、澳洲和美洲加勒比海的西印度群岛,目前世界上以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和美洲的格林纳达两地产量最 丰。
肉豆蔻的果实有一层硬壳,成熟后呈黄褐色,可用来制作豆蔻核仁和肉豆蔻皮两种香料。果仁榨取的肉豆蔻油,系香精油中的一类。肉豆蔻皮磨碎成粉,可作为食品,或作为菜肴的调味品。肉豆蔻还有药用价值,果仁所含的肉豆蔻醚可产生致幻作用使人兴 奋。
肉豆蔻树是在12世纪时传入欧洲的。至于英文为何选用Mace这个词作为权杖之名?其间是否存在语言学上的联系?不详。估计最大的可能是肉豆蔻的果实形状以及挂在枝头上的模样,与权杖头非常相似(图 0.1)。
权杖最早产生于西亚,早期的功能为工具或兵器,有击打功用,可用于狩猎劳作,亦可作为部落社会间族群械斗的兵器或防身器具。后来逐渐衍生为特殊的礼仪用具,并附加神圣的属性,成为国王、郡主、酋长、军事首领、宗教祭司、长老、精英贵族等社会上层人士手中所持的器具,并作为王权、身份和地位的象 征。
权杖出现在前陶新石器时代,其源头很有可能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期的权杖头均为石质,材质普通,硬度不是很高,造型朴实无华,多作圆片状、扁球形、椭圆形、梯柱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功能的转化,人们开始追求原料质地和色泽纹理,造型也转而以球形、梨形为主,也有一些制成斧形、鹤嘴锄、棍状、十字形、花瓣状等形状。制作工艺考究,精雕细琢,器表开始装饰花纹,凿出乳状瘤突、蘑菇头、锥突或尖刺,甚至还有的浮雕、圆雕人物、动物,乃至镌刻文字,以表达某种愿 景。
进入红铜时代以后,开始流行红铜、青铜铸造的权杖头,甚至用金(或表面鎏金)、银、铅和铁制作权杖头。还有一些使用了新型材料,如象牙、费昂斯、1琉璃(玻璃)、玛瑙、水晶、青金石等,造型和装饰花样迭出,以至于镶嵌珠宝,尽显奢华。尽管权杖头的材质不断创新,但传统的石质权杖头并未衰落,而与使用新材质的权杖头长期共存,两者各自扮演不同的功能角色,从远古一直走到现 代。
在西方,象征君权统治的权杖也称“节杖(Scepter)”,可见权杖和节杖在语义上是有区别的。Mace语境下的权杖似乎更强调其原始性,质地普通,做工粗放,装饰简单,年代距今较久远(图0.2:1)。Scepter语境下的节杖似乎更注重其现代性,质地贵重,做工精良,装饰豪华,多指近现代象征王权和指挥权的王杖(图0.2:2)。西方还有另一类性质的权杖,因其杖首形状呈回旋弯曲的问号或螺旋状,被称为“曲柄杖”。此类权杖系天主教、基督教主教或修道院院长、教会长老等宗教上层人士所持,英文称之为Crosier,汉语译作“牧杖”或“权杖”(图0.2:3)。据传,曲柄杖起源于基督教,其祖型就是耶稣手中所持的那柄“牧羊杖”,其功能是表明持有者在宗教界所具有的特殊身份和地 位。实际上,类似器物最早起源于古埃及法老所持的一种权杖。
本书讨论的内容仅限于权杖的第一类,即Mace。所关注的焦点为装置在杖柄顶端的权杖头(Mace-head),也会少量涉及节杖(Scepter),曲柄杖(Crosier)则不在本文讨论的范畴。此外,还有一些被认为是权杖的器物,实际上并非权杖,本文也将对其做出适度的甄 别。
自序
我对权杖的了解可追溯到在北京大学读本科时。1980年,我们历史系一帮同学排演了希腊著名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the King),导演是考古专业77级的柳元(1957—2020)。因剧中主角俄狄浦斯王手中要拿一柄权杖作道具,为此他想了个辙,将一个小药瓶插在木棒的顶部,用纸将其包裹成一椭圆球,权杖头表面和杖柄再包裹一层金纸,一件有模有样的权杖就成形了(图I.1)。在北大办公楼正式演出时,我负责舞台灯光,这件权杖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 象。后来我在美国也和柳元就权杖的起源有过讨论。
1986年,我和同学水涛前往甘肃河西走廊调查,曾采集数件权杖头残件。1987年,我俩再度联手发掘了酒泉干骨崖墓地,我亲手挖出一件白色大理石权杖头,当时也没觉得特别。1999年,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访问学者,有一天去学校博物馆参观,在西亚展厅,远远看到展柜里有一件白色的权杖头,恍惚间竟误以为是我挖出来的,简直是太像了。回过神来仔细观摩,这件权杖头的表面竟然刻有楔形文字。那一瞬间给我震撼极大,自此开始关注此物。
2000年初,应伦福儒(Colin Renfrew,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之邀,我去剑桥大学参加“欧亚草原学术研讨会”。返回美国前需在伦敦等待美国大使馆签证,碰巧陕西省在大英博物馆举办中国文物展,在刘云辉副局长热心帮助下,我得以在博物馆后楼随展人员的一个大房间借宿。那两天没事就去博物馆,看到不少出自西亚、埃及等地的精美权杖头,眼界大 开。
2001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举办“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报告了权杖的初步研究。2002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西安举办“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再次作了有关权杖研究的报告,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并引发网上热议。2后来,甘肃省博物馆举办“丝绸之路”出土文物大展,专门派了一位副馆长到北大找我,我将自己搜集的资料都提供给了他们。这方面的内容随之成为大展的一个亮点,不仅增加了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内涵,也扩大了学界对权杖这一文化特质的关注。2011年,为庆祝宿白先生九十大寿,我撰写了《赤峰及周边地区考古所见权杖头及潜在意义》一文,3将研究的视角扩展到北方长城沿线。如今回过头来看,以上旧文还有欠缺,将权杖一律视为王权象征的看法也过于绝 对。
最初,我的计划是就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古发现,讨论权杖的来源、功能及此物背后东西方早期文化交流的历史。为此从20世纪末,我开始奔走于国内外大学、博物馆和图书馆搜集资料,历时近20年,耗费大量精力。想不到的是,几易其稿,文字数量竟然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远远超出了当初的设 想。
权杖这一文化特质产生于近东,后来逐渐扩散到欧洲、北非和中亚等地。这个文化特质的奇特之处在于,最初它就是普通的工具或兵器,后来才逐渐衍生为威权的象征。这两方面功能也随着权杖的传播,蔓延到世界各地,而且延续时间甚久,至今仍在一些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是在其他任何单体文物上很少见到的文化现象。更为有趣的是,距今4000年前,权杖东传至中国,早期仅在西北地区流行,后有少量流入中原,并被夏、商、周三代部分社会高层接纳,与斧钺和青铜礼器等华夏传统礼器并列,作为王权和身份的象征。及至战国时期,权杖作为象征威权的功能渐次式微,并以兵器和仪仗的形式在华夏大地延续下来。
我之所以迷上权杖,是希望透过这个看似不甚起眼的文物,见微知著,深入考察人类社会自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特别是世界体系初步形成以后,欧亚大陆的族群迁徙和不同文化互动交融的历史,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发展变化。同时希望通过这方面的探讨,进一步推动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研究,特别是由此引发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东西交往,对中国早期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产生的推动作用的思 考。
2017年,我曾就本书的初稿征求李零先生和杨泓先生的意见。李零先生希望我最好将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历史时期,对先秦时期的“殳”和历史时期的“骨朵”等器物作些比较研究。杨泓先生则建议我再看看《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相关内容,并热心地给我介绍了“殳”“骨朵”“金瓜”等文献资料,还就书稿中的某些措辞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为此,我在原书稿的基础上增加了后两章,将研究的下限延伸到历史时 期。
本书行将付梓,感触良多,竟不知从何谈起。感谢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李零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冯时教授的热情推荐,上海古籍出版社申请到出版基金,使本书得以出 版。
本书的写作耗时甚久,其间先后得到多位国内外师友、同仁和学生的帮助。感谢梅维恒(V. Mair,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伦福儒、奥利维(Laurent Olivier,法国国家考古博物馆)、罗森(Jassica Rawson,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吉迪•谢拉赫—拉维(Gideon Shelach-Lavi,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教授)、傅罗文(Rowan Flad,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的热情邀请,使我有机会在美、英、法、德、以色列等国访学、搜集资料。感谢巴尔—约瑟夫(Ofer Bar-Yosef,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为我提供希伯来文(Hebrew)的研究论文;感谢哈克(Yitzchak Jaffe,以色列海法大学)博士为我翻译希伯来文资料并提供帮助;感谢罗泰教授为本书翻译英文目录和英文摘要;感谢温成浩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我搜集西文书刊资料并帮助修订本书的参考文献;感谢宋蓉副教授(北京联合大学)为本书制作主题索引;感谢万翔副教授(西北大学)对主题索引和小语种外文的审定。
为我提供帮助的还有下列女士、先生,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郭大顺(辽宁省文化厅),林小安(故宫博物院),刘楠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覃春雷,李小波(四川师范大学),水涛、张良仁(南京大学),伊弟利斯、李文瑛、胡新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国瑞(新疆文旅厅市场处),种建荣(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刘旭、闵锐(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哈比卜(西藏自治区罗布林卡管理处),王辉、秦小丽(复旦大学),萨仁毕力格(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刘冰(内蒙古赤峰市文化局),杨泽蒙(内蒙古鄂尔多斯博物馆),陈国科(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德芳(甘肃省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政府参事),马强(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杨建华(吉林大学),包曙光(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罗丰、马健、梁云(西北大学),吴卫红(安徽大学),谢尧亭(山西大学),吴晓筠(台北故宫博物院),常怀颖、高伟、艾婉乔、王鹏、何毓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丁见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颜海英、贾妍、孟繁之、陈建立、陈冲、方笑天、杨月光(北京大学),Christoph Kremer(德国波鸿大学),刘艳(英国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唐小佳、刘睿良(英国剑桥大学),李秀珍(英国伦敦大学),俞雨森(德国海德堡大学),涂栋栋(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杨妍(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苏昕(美国哈佛大 学)。
最后特别感谢李零教授为本书题签。
2021年1月于北京蓝旗营

